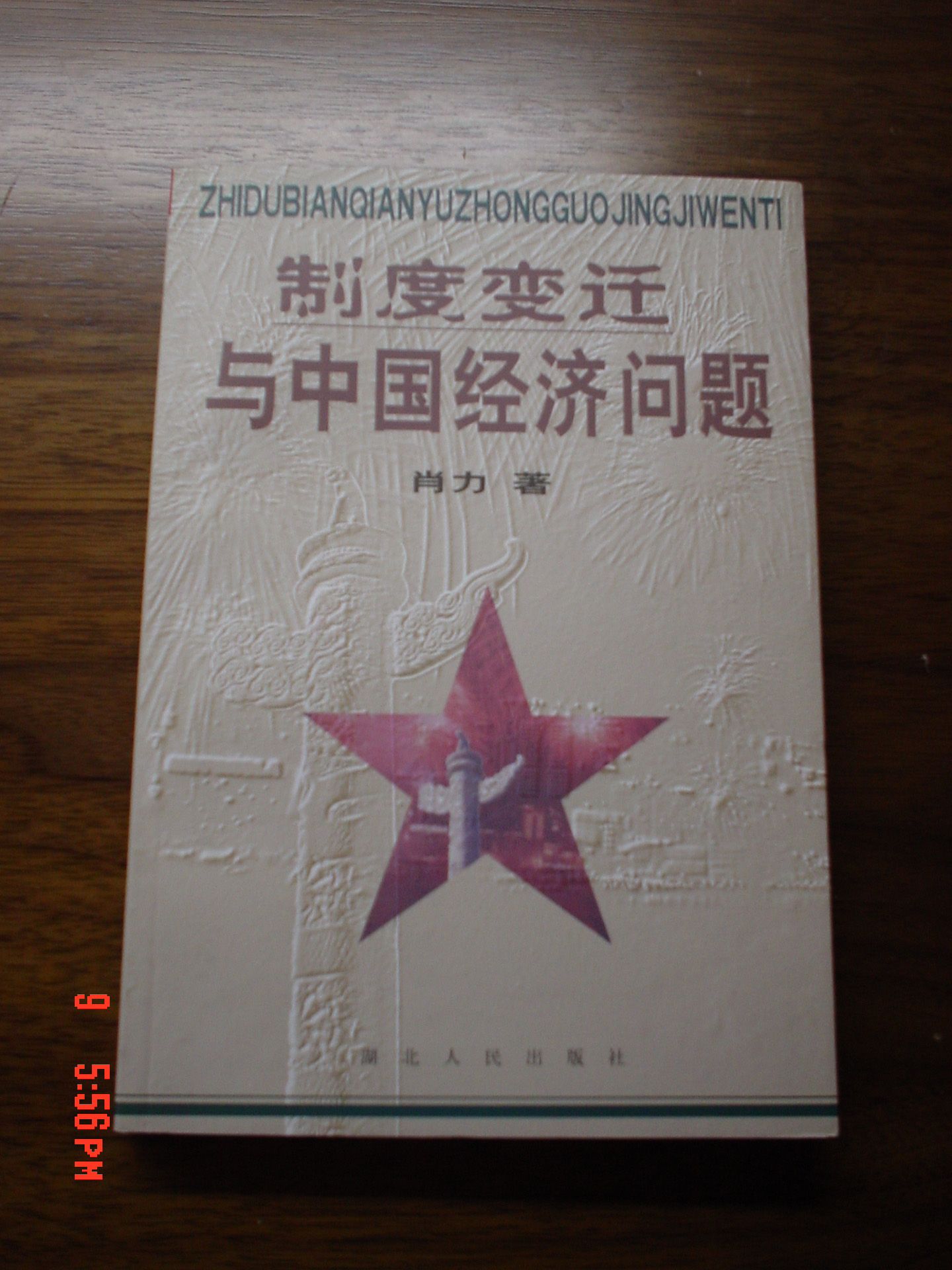|
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一直企圖以傳統(tǒng)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局部均衡分析方法研究交易機(jī)制,這是不可能成功的。因為如果允許交易機(jī)制成為內(nèi)生變量并且按照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分析依賴于信息不對稱結(jié)構(gòu),那么其它三個結(jié)構(gòu):技術(shù)、偏好、資源稟賦(Endowments)都難以保持其外生變量的性質(zhì)。這樣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局部分析”的“一般均衡”基礎(chǔ)就不能維持而失去其本身的意義。如果想以均衡分析來研究制度演進(jìn)進(jìn)程,那么上面的分析方法行不通,使得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的進(jìn)一步發(fā)展陷入一種窘境。因此,我們有必要進(jìn)行有關(guān)理論創(chuàng)新。博弈論(Game Theory)可以說是近來最頻繁地出現(xiàn)在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和社會學(xué)家等的論著中的詞匯之一。這不僅是因為它為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的發(fā)展所帶來的勃勃生機(jī),而且還由于它在政治學(xué)、國際政治學(xué)、社會學(xué)、倫理學(xué)和犯罪學(xué)等社會科學(xué)領(lǐng)域內(nèi)的廣泛應(yīng)用。社會中人們之間的一切相互行為、相互合作、相互沖突、相互欺騙、相互敵對、相互競爭和相互交易等互動行為的總和都可以看作是人們之間所進(jìn)行的博弈。所有涉及這種人類社會現(xiàn)象都可以用博弈理論來分析、說明和解釋。從博弈論的角度考慮,可以把制度定義為一套在“多次博弈”之后形成的、使人們在發(fā)生互動關(guān)系時較確定地了解別人行為方式的社會契約。博弈論的研究方法即是對現(xiàn)實的歸納和總結(jié),同時它又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認(rèn)識和解釋制度。這要求廣泛地使用博弈理論,尤其要在遵循博弈論思想的前提下,使用博弈論的具體分析方法。 《制度變遷與中國經(jīng)濟(jì)問題》在科斯、諾思、布坎南、奧爾森、阿爾奇安、德姆塞茲、威廉姆森、張五常等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大家與汪丁丁、張宇燕、張維迎、周其仁、 盛洪、樊綱、張軍、林毅夫、張曙光、唐壽寧、汪新波等中國經(jīng)濟(jì)學(xué)家近年來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礎(chǔ)上,用博弈論的具體分析方法探討制度的產(chǎn)生與變遷,尤其著重討論了一直被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所忽視和分析不足的問題。作者借用囚徒困境模型(Prisoners' Dilemma)探討了制度的產(chǎn)生與變遷。他認(rèn)為理性選擇的社會制度模型(其分析方法承自于新古典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基本方法)并沒有充分說明這種在從模型到說明再到理論和解釋的過渡中所作的假設(shè)的合理性。并在用具體的博弈模型時,通過不同的前提條件,給出制度的產(chǎn)生與變遷的三種獨到解說,同時也著重探討了在復(fù)雜的社會關(guān)系中人們互動行為的重要社會特征的不同方面,這些也是導(dǎo)致產(chǎn)生制度變遷的過程的主要因素。(多方面行為特征可解釋為博弈結(jié)果的多重性,正是多個可能的制度均衡才意味著社會的變遷。)該書的其他章節(jié)也大都是運(yùn)用博弈論的語言對中國正規(guī)的制度的變遷作的闡釋。博弈論作為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的分析工具是經(jīng)濟(jì)學(xué)理論的又一次創(chuàng)新,它的確幫助我們澄清許多對制度的模糊認(rèn)識。在博弈論看來,不論是正規(guī)的制度還是非正視的制度,都是由一些均衡預(yù)期行為組織成的。就是說,它們都是博弈的均衡結(jié)果。博弈論最基本解的概念——納什均衡--是50年代由J.納什(1994年諾貝爾經(jīng)濟(jì)學(xué)獎獲得者)提出的。但是納什均衡還只是一個最粗略的解概念。其實對一個具體博弈我們最大的擔(dān)憂不是該博弈無解,而是往往有多個均衡解。對于這種問題,博弈論專家的解決方法是,在現(xiàn)實生活中,參與能使用某些被博弈論模型抽掉的信息來達(dá)到一個“聚點”均衡(focal point equilibrium)。在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中,信息就可以解釋為參與一個社會必須存在的“道德傳統(tǒng)”(D.諾斯稱之為“文化意識型態(tài)”),從而可以決定在多個納什均衡中會出現(xiàn)某一個特定的均衡。此處的聚點(focal point )作用被解釋為:當(dāng)參與人之間沒有正式的信息交流時,他們存在于其中的“環(huán)境”往往可以提供某種暗示,使得參與人不約而同地選擇與各自條件相稱的策略(聚點),從而達(dá)到均衡。這也就與D.諾斯理解的非正規(guī)約束的作用一樣了。在D.諾斯的分析框架中,文化作為一組“通過教育和模仿而傳承下的行為習(xí)慣,對各種制度變遷產(chǎn)生影響”,文化的作用對形成“聚點”均衡的貢獻(xiàn)尤為突出。也是作者在其文章中也使用一個博弈模型進(jìn)一步討論了在不完全信息條件下,交流對形成“聚點”均衡的重要性。因此,當(dāng)一個特定的博弈達(dá)到均衡以后,參與人就會對這一新的均衡(即我們所說的新的制度)作出自己的解釋并修正自己的行為,從而為下輪的博弈作準(zhǔn)備,那么制度的變遷就完全不同于以新古典方式構(gòu)建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理論所作出的解釋,制度變遷在此處被看成為一種均衡狀態(tài)向另一種均衡狀態(tài)的演進(jìn)。 以博弈論思想作為研究制度變遷的分析方法,為新制度經(jīng)濟(jì)學(xué)家們提供了解釋制度變遷的新思路。但是,有關(guān)博弈論的許多理論如合作博弈等仍需進(jìn)一步發(fā)展,否則,尋找博弈均衡仍是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 |